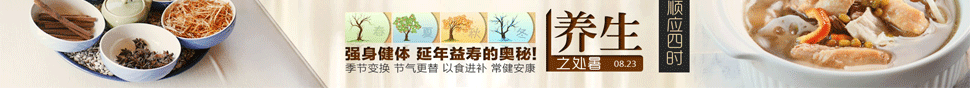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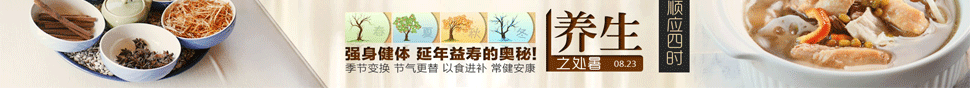
一、引言
尊亲属,作为“尊尊”与“亲亲”的二元结合,尤其是父系直系尊亲属,在中国传统法制中具有特殊地位,被视为纲常伦理最核心的表现,这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本质所系。在传统礼法架构下,“尊尊”强调的是宗族中辈分、年龄、地位之尊崇,“亲亲”强调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之亲近。服制入律后,出现了按服制亲等远近,对弑亲行为施以不同梯度刑罚的律法内容。杀尊亲属罪,即为传统中国刑律中的伦常条款,贯穿整个中华法系时期。不论在立法规制还是司法适用层面,历代律法均将其入诸重罪。如专条科罪的《大清律例》。
晚清修律以来,中华法系解体、传统礼法体系随着西方近代法学理念转向,杀尊亲属罪也走上近代转型之路,尊亲属的法律特殊地位渐被剥夺。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在更为复杂的矛盾旋涡中挣扎浮沉,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的双向拉力中艰难迈步。这一时期的立法规制与司法实践亦呈现新旧杂陈的特征。但经过清末以来二十多年西学影响与辛亥革命的政治洗礼,特别是经过民元制度实践,司法独立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司法独立攸关全国“治体命脉”,为法治国第一要件,成为有识之士之共识。据此,黄源盛教授在梳理传统与晚近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侧重探讨了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一系列伦常条款(如第条“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等)的沿革与存废、伦理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等立法理论问题。囿于种种原因,司法与立法并不能亦步亦趋。面对杀尊亲属条的立法文本变动,民初司法实践如何调适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构成对民初司法制度理解的又一面相,也体现司法官对近代法制转型问题的思考。
二、立法规制:伦常为重,兼顾国情自清季礼法之争以来,围绕尊亲属的概念范畴的相关论争不止,立法文本反复逡巡。民初虽仍沿用服制图来划定亲属范围,但以刑事立法原理与技术而言,《暂行新刑律》与传统旧律之间的差异明显,除了有关宜否另立专章等编纂体例问题,杀尊亲属罪也作出实质意义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于文例中对尊亲属概念予以廓清。晚清修律时有地方督抚曾于签注中直言修律虽应着意维护伦理法益,但除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属以及期、功尊长之外,传统律典并未对尊亲属作出十分清晰的外延界定,尊亲属及亲属的称谓散见于刑律各条之中。故《新刑律草案》于第八十二条特别作出明文界定。直接脱胎于《钦定大清刑律》的《暂行新刑律》,对尊亲属的概念也其来有自,明确将外祖父母排除适用。至年,袁世凯令章宗祥、汪有龄、董康等人筹备法律编查会以修订刑法,虽有《修正刑法草案》匆匆告竣但并未生效颁行,但特于直系尊亲属内加入外祖父母一项,这一改动值得注意:“第八十条:称直系尊亲属者,谓左列各人:一、高曾祖父母。二、祖父母。三、父母。四、外祖父母。”
旧律,外祖父母服属小功五月,但传统官府断案时,往往将外祖父母与期亲尊长并重,以尊亲属论。之所以将尊亲属的概念外延扩展至外祖父母,主要在于刑事法益的调整:一则欲使外祖父母的新刑法定位与服制等级相符,二则考虑到世界各国通行的男女平等主义观念:“东西各国民法,母党与父党并尊,外祖父母为母之所自出,中国服制虽属小功,而刑律人命斗殴诉讼各门,与往往期亲尊长并论,且有上同祖父母父母者,因母之所尊而尊之,初不得疑为二本也。”本条附后修正理由对这一立法原意表示认可:“亲属例原案,仅尊亲属及亲属两项,至为简单,今亲属加重不仅限于直系,原案无外祖父母一款,外祖父母服虽小功,究系母之父母,在旧律,犯谋杀与祖父母父母同科;犯殴杀亦同期亲尊长。原案以母系斥之,误也,今增入。”
当时的法学人士普遍认为,修正案所增内容多以维护纲常名教为要,依据伦常定罪量刑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吴贯因对此直言:“此纯就中国的旧教义立言,是家族主义、君权、父权思想的表现,本质上是反个人自由的。”周冶平将此番修正案对礼教的维护归因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此一修正案完全迎合袁世凯的意旨,……在思想上可以说是返古的,带着礼治的帽子,而行威吓镇压之实。”
至年,董康、王宠惠任修订法律馆总裁后,以《修正刑法草案》编订《刑法第二次修正草案》时,对尊亲属外延又做出扩张性调整,重申将外祖父母列入尊亲属概念范畴,意在与前清旧律、修律大旨作一分别:
外祖父母在旧律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殴期亲尊长、骂尊长均与祖父母同,故前法律馆草案、修正案及宪政编查馆核定案皆以外祖父母列入尊亲属中,嗣后经资政院议决删除,其意谓外祖父母为妻亲,已包括于亲属之内,而不知对于尊亲属犯罪则刑有加重,而对于亲属犯罪则只有免除及减轻,其用意不同,故本案拟于尊亲属增入外祖父母。
其二,拟制妾之亲属地位。在新的社会法律体系中,相对于家长的子孙而言,妾的地位究竟如何定义,如何对其权利义务给予立法与司法上的回应与确认,是一项无法回避的议题。传统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形式上终结,倡行男女平等自主的婚姻观念,但妾仍是客观存在的家庭成员与社会群体。民初曾先后任教于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的法学家江镇三据此主张:“民法于妾之地位生活及妾之生子女前途,均间接设有救济之条”,大理院民事判决例虽已明确妾的法律身份“妾不能为家之尊长”,但妾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仍应作为家属之一员,“应与其他家属同受相当之待遇”,这些是民初新民法规则为解决实际社会生活问题的折中之举,处理刑事纠纷也类似,若刑事规则呈空白状态,既令司法官无法可依,又令民众无所适从,于近代转型的平稳过渡亦无益处。故当以亲属论时,《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第十二条将妾的刑事法律地位拟制为妻的法律地位:“刑律第八十二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一款称妻者,于妾准用之。第二百八十九条称有夫之妇者,于有家长之妾准用之。”
这意味着,只要妾之家长(丈夫)拥有子孙,刑事规则便承认妾在家中的长辈地位,准许妾拥有类似于母亲的拟制法律地位,享受家属待遇。实际上是间接承认妾在刑法上的尊长尊属地位。这一法律拟制,既是民国刑法对社会民俗的一种宽容态度,也是对人伦亲情的回护。毕竟法令、法理念可变,但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长幼之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取缔的人际关系。或许在帝制中国,受困于君权的三纲五常将这种长幼之序推向了极致与僵化,但以平等进步自诩的民国,可以终结传统帝制为历史使命,但不能以反对最基础的人伦为目标。
民初对尊亲属的立法纂修经历了“温故与知新”的时期,既以伦常为重,又能兼顾国情,但伦常与国情之间同样存在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每一次刑律草案的编订都意味着国情与伦常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在以伦常为重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去兼容国情,故方有董康对北洋时期的刑法修订“凭事实为修正值标准”之语。与此同时,尝试引入平等的西方法理念去逐步淡化尊亲属的特殊地位,借助新刑事立法技术对尊亲属概念加以廓清,立法者的审慎既是选择也是犹豫,司法者也需要为平衡各方利益有所为有所不为。司法实践中的杀尊亲属罪面临何种问题,如何在解决社会问题、司法纠纷的同时将法制转型向前推进,下文将以同时期的大理院刑事判例为据观察司法官的回应与尝试。
三、定罪科刑中的纠错与造法新旧交替时期,法律变动很大,民刑法典尚未颁布,民国政府不得不援用前清法制、适用仓促植入的欧陆法制,此番运作必然引发诸多疑义。在整个北洋时期,尽管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家真正统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由于政权更迭所形成的中央权力真空,法官裁判案件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大。大理院在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因它是通常的最高审判机构,更由于这一时期作为民国正式立法机关的国会在多数时间不能进行正常的立法活动,在转型期法律规范尚待完备的情况下,大理院通过“法律审”,进而发布判决例和解释例,承担了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的职责,也承担了相当部分的“造法”职能,其在中国法律和司法近代化过程中实具特殊地位。那么此时大理院推事对杀尊亲属罪如何定性?如何裁断杀尊亲属罪?司法官会遇到怎样的问题?他们又是尝试用什么样的新法理来裁判此类案件?这需要从司法判决书汇辑中所搜集的杀尊亲属案件来实证考察。笔者所参阅的北洋时期的判决书汇编主要出自黄源盛先生纂辑的《大理院刑事判例辑存》、郭卫编辑的《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和《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周东白编辑的《大理院判例解释四:新刑律汇览》等。
从大部分判例和解释例中可见,司法官承认弑亲行为有乖伦常风化的大前提,但在科刑方面,大理院能够严格以新订刑法为据,对尊亲属身份释疑、严格限定适用、尊重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对错判案件及时撤销或改判,对刑法未作明确规范的空白区以判决形式进行“造法”,着意淡化杀尊亲属条款的适用、力求去特殊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下面分述几起案例。
(一)案例一:王李氏谋杀其夫王满库案
本案案发于年间,行为人王李氏与被害人王满库为夫妻关系。王李氏与田兴江通谋,将王满库杀死后藏尸逃逸。本案由独石县进行了第一审判决,依《暂行新刑律》第条“伤害尊亲属致死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判王李氏所犯之杀夫行为为伤尊亲属致死罪,处王李氏无期徒刑。
其后,察哈尔都统署审判处在覆判程序中认为本案的定性没有问题,犯罪行为对象王满库是犯罪行为人王李氏的丈夫,即夫为妻之尊亲属。但在罪名认定和量刑上不妥,应直接判以“杀尊亲属罪”,判处王李氏死刑。故作出改判:本案应依第条杀尊亲属罪处断。
年,总检察厅检察长以一审判决与覆判均属违法,提起非常上告。上告理由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夫不属于尊亲属范畴。具体阐述如下:
查此案王李氏与田兴江公同谋杀其夫王满库身死,系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罪,初判认为伤害尊亲属固属不合,覆判改依第三百十二条处断,是仍误认为夫为妻之尊亲属。
总检察厅检察官汪祖泽发表详细意见认为,察哈尔都统署审判处所引尊亲属条属于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改判:
查刑律所称尊亲属,以同律第八十二条所列举者为限。本案王李氏谋杀其夫王满库身死,显系触犯第三百十一条之罪,原判误认夫为妻之尊亲属,援照第三百十二条处断,殊属引律错误。……应请将原判违法之部分撤销,改照刑律第三百十一条处以无期徒刑。
对于总检察厅的上告意见,大理院予以采纳,并于年12月6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内容如下:
察哈尔都统署审判处认定事实,称:“……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夜间,王李氏、田兴江共同将王满库杀死,藏尸山药窖内,用土掩盖灭迹,均各逃逸,经汎获案送审,由独石县判经判依刑律三百十四条处王李氏无期徒刑,并依刑律补充条例并科奸罪,定执行无期徒刑。”案经覆判,于王李氏杀人之所为改用刑律第三百十二条,仍定执行无期徒刑,总检察厅检察长提起非常上告。
据以上事实,王李氏实为杀死王满库之共犯,依刑律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王李氏应依同律第三百十一条科断;……乃原判误认为夫为妻之尊亲属,依刑律第三百十二条科断,固与同律第八十二条第一项各款所规定者不合;……属违法。总检察厅检察长依法提起非常上告,自系合法,总检察厅检察官汪祖泽之意见亦属允当,应即由本院将原判撤销。王李氏杀人之所为依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三百十一条处断。
固有礼法观念的强大与中西司法制度的冲突显而易见。传统官府在审理案件时,妻妾因奸杀夫,均以杀尊亲属罪论罪,并处以斩、绞或凌迟之极刑。尽管《暂行新刑律》总则文例中明确将夫排除于尊亲属的适用范畴之外,但本案的一审与覆审法院的审案思维仍与传统无二,习惯性地将夫定义为妻之尊亲属。
这也难怪,本案虽案发于光绪年间,但主要审理时间是在北洋时期。年许世英去职,梁启超继任司法总长伊始,由于人才、经费两缺,主张推行消极的司法建设路线,在县级地方政府实行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年4月5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各县的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县知事审理案件得设承审员助理。”实际情况是,在不少州县,直接由传统旧制或是在县署分科治事改革的基础上改为县知事兼理司法。这一时期施行的基层司法制度即为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
本案的一审程序是在一个叫“独石县”的地方完成的。不论是司法兼理行政,抑或行政兼理司法,司法与行政合一是中国古代地方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但司法是各级官府的核心职能,用“司法官兼理行政”比“行政官兼理司法”归纳官府职能更准确。传统州县诉讼制度与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都是靠县衙门的正堂官处理诉讼事务,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即意味着由行政官兼理司法。传统旧制下,知县作为父母官,通常以私人名义聘请幕友协助处理刑名事务,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县知事延续传统官府的审理思维和习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有别于基层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普遍欠缺,大理院和总检察厅所属推事、检察官的任用要件非常严格,大理院推事中曾负笈游学者,大多为旧学已仕人才,对经史子集即传统旧律均有相当根底,江庸因而有民国司法“人才整齐,胜于其他机关”之语。
概要言之,大理院和总检察厅的司法人员学识与能力迥异于当时的基层审判机构,已具备了较为深厚的西方法学素养,罪刑法定的意识较基层司法官员更为严格,因此能够及时按照《暂行新刑律》的新规则,对杀尊亲属罪的审理予以纠错和规范。
(二)案例二:邢连弟杀死族叔邢玉田案
本案于年7月19日由直隶高等审判厅进行了第二审判决,最后上告到大理院,大理院于年8月26日做出终审判决。从本案的终身判决书归纳出本案案情大致如下:
邢连第与邢玉田同村居住,邢玉田为族叔。年9月5日,邢连第因邢玉田筑埝挡水,损害其地内稻禾,与之发生口角斗殴,彼此俱未成伤,各散回家。邢连第回家后气忿不能释怀,晌午时瞥见邢玉田站在街上,遂回家持取尖刀,乘邢玉田不备,将其右臀连扎两处,邢玉田当时倒地。邢玉田之母邢路氏瞥见喊救,邻人邢荣、邢保弟闻声赶来,邢玉田已因伤重毙命,邢路氏即赴县呈讼。
在一审程序中,该县正堂依《暂行新刑律》第条“杀尊亲属罪者,处死刑”之规定,判定邢连第杀死族叔邢玉田之行为所犯为“杀尊亲属罪”,科处邢连第死刑。邢连第不服判决,提起控诉,要求改判。控诉审法院审理后,改依《暂行新刑律》第条普通杀人罪判处邢连第死刑,邢连第仍不服判决,提起上告。
大理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原判在引律和量刑方面皆不当。第一,依第条“杀尊亲属条”定罪,是为定罪不当;第二,将刑名改依第条判为“普通杀人罪”之后,仍处以极刑,是为量刑不当。理由如下:
首先,上告人邢连第杀人行为事实非常明确。其用刀连扎邢玉田两下,邢玉田伤重身死,不能以受伤处所在为右臀并非要害致命之处为理由,辩称行凶时仅有伤害之故意,并无杀人之故意,以图改变刑罚。
其次,本案肇事原因,系斗殴口角,即由邢玉田筑挡水、损害稻禾在先而引起的,邢连第因一时激怒而斗杀其人,犯罪恶性与蓄意谋杀自有轩轾。
为求情罪允协,大理院最终将原判关于主刑的部分先予撤销,再行改判。上告人邢连第杀死族叔邢玉田之所为,应依《暂行新刑律》第条判为普通杀人罪,并处无期徒刑。
笔者认为本案控诉审法院和大理院的态度界于半肯半不肯之间,对刑名更换认定的说理也并不充分。按民初刑事诉讼程序,控诉审法院会针对提起控诉理由进行司法审理,并不是就案件的整体进行全面审查。而控诉审法院却并未就杀尊亲属罪改判为普通杀人罪的理由加以说明。大胆地推测一下,族叔为服制内尊长,既然判决书中并未对其尊亲属身份提出异议或加以纠正,则在尊亲属的身份认定上不太可能出现错失,或者说因为是基于非血缘的收养、过继等关系而产生的拟制亲属关系(如嫡母、养父),给尊亲属的身份认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需结合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生活等要素加以分析考察之后再下定论;经控诉审程序改判之后,刑名发生变动,但科刑仍为死刑,更像是对杀尊亲属这一特定刑名的一种回避姿态;大理院也只是简单地以一句引“引律既有错误”轻轻揭过,但具体是哪条律文援引错误,则说理不明。与传统官府不分已行未行皆对杀尊亲属的行为施重惩以昭炯戒的审理方式相比,显然,大理院及控诉审法院此举有反其道而行之之意。北洋时期,司法独立是时代的主调,大理院在独立审判方面,所有审判案件竭力做到不许外力干涉请托,一扫旧时司法舞弊之弊端,超然于政潮之外,曾为民国司法带来一丝曙光。因此,可以排除大理院司法不公的因素。
大理院对此案的处理,很有可能与其所面对的近代法制环境有关。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形式上是从专制迈向共和;实质上是从集权统治到权力分属,法律制度的新旧递嬗,整个司法界所面对的,是新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法意识的剧烈变动与发酵。这样的历史机缘自然千载难逢,司法人士于彼时的风风雨雨中犹思积极振作,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坚持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在法有空白的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发挥司法能动主义之精神,对存在疑义的案件作出符合新法制理念的裁断,将以新代旧的法制转型向前推进一步。
本案中的控诉审法院和大理院对杀尊亲属行为的定罪和量刑都做出了与传统官府审断大不同的处理方式,正是在对杀尊亲属罪实施司法适用上的改造,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间,司法界的价值取向。在下面一起案例中,大理院便是通过判例要旨的方式行使了“造法”功能,以区分婚姻的形式要件与事实要件的方式,确立了继母作为尊亲属的身份适用准则。
(三)案例三:卢声才杀何氏案
年10月30日,安徽高等审判厅就卢声才杀害何氏一案,作出二审判决,以杀尊亲属罪为断。本案案情比较简单,卢声才为占有钱财,用剪刀猛戳何氏肚腹等致命部位,致其毙命。一审二审法院以其杀人之犯罪行为认定无误,均判以杀尊亲属罪。但卢声才在二审后提出上告,对被害人何氏的身份认定提出疑义,认为何氏虽有后母之名,但其与卢家成的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不得以杀尊亲属罪为判,应改判为普通杀人罪。
从大理院的判决主文来看,被害人何氏与犯罪行为人之父卢家成虽无婚书,但存在事实上的同居关系,这种同居关系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以及对这种同居关系如何认定,直接决定了被害人何氏对犯罪行为人而言是否具有尊亲属的身份。大理院认为:应根据民法规定进行严格解释,将婚姻限制定义为“定婚”,定婚以婚书为必备要件,卢家成虽娶何氏为继配,但无婚书,定婚无效,自然,二人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显然,其法律后果便是何氏不能以继母之身份成为卢声才的尊亲属。
按现行律载“男女订婚,写立婚书,依礼聘娶”,又载“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等语。是男女仅为事实上之同居,而于上述要件苟无已具备,在法律上既不发生婚姻之效力,而其夫妇之关系亦属无可成立。
上告人虽供称“何氏是我后母”,卢家成供称“何氏是我续弦的女人,是我的继配”,然实际上,何氏对于卢家成已否取得妻之身份,仍应就其定婚之时具备法定要件与否为断。卢家成在第一审所称:“他(指何氏)先在王家,丈夫死了,我在胞母舅那里认识,彼此愿意也无婚姻关系,他算是跟我的,无婚书。”在原审所称:“他跟我的,并没有婚书,也没有媒人,不过是两下愿意的”云云,固难免有意避就回护其子。
不过,从证人证言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没有婚书这一法定形式要件,但按照民间礼俗,何氏嫁入卢家的婚配程序已经完备。既有媒妁之言,卢家也下了聘礼、上门迎娶、在当地已办过婚宴,亲邻都认定卢家已经娶何氏为继配、何氏亦有“后母”之称谓,这些都是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佐证:
但据被害人之妹何氏供:“我姐姐是王锡九、卢家旺作媒的,说定四十块钱聘礼,也是用轿子送上门的,卢家也请过客”,则当日既有媒妁、受有聘财,且经依礼聘娶,虽王锡九等业已物故,而其戚族邻佑中年事稍长者习知事者应自有人,倘予传讯,未始不可证明,原审仅以卢家成等有继配后母之称谓为认定之唯一根据,其审理事实究欠完密,上告意旨就此有所攻击,自非全无理由。
那么根据民法亲属编之相关规定,卢何二人的婚姻是否于法律上成立呢?实际上,大理院在年的两则判决例中分别出具过男女定婚、成婚与否,优先尊重当地婚俗习惯的司法意见。
首先,定婚要件可以是婚书,若存在婚书争议问题,则依地方习惯判定:“男女定婚虽非以婚书为唯一要件,而依靠婚姻律沿革及一般习惯大都重视婚书。苟当事人关于缔婚之书件有争,自应根据各该地方习惯,以定婚约是否成立之标准。”
其次,成婚与定婚的法律效力稍有分别。定婚后须完成某些特定仪式,婚姻方得成立:“婚姻成立与定婚有效,系属两种问题。婚姻成立必须经习惯上一定形式,其经一定仪式而成婚者,乃新刑律重婚罪成立之要件。故仅定婚而尚未成婚更与他人成婚者,即不得以重婚论。”
根据被害人何氏之妹的证词,只需大理院到本案当事人居住地走访调查一番,卢何之婚的确认并不是多大的司法难题。
但实际情况是,年1月31日的大理院回避了年的这两则判决例。诚然,大理院判解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至今尚无定论。至少在本案所涉及杀尊亲属案件中,大理院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根据四级三审制,在本案中处于终审法院的大理院,为了将原判杀尊亲属罪撤销发回改判,采取了限定解释的方法,认定何氏与卢家成的事实婚姻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裁判事实婚无效。何氏不能认定为卢声才之继母,原判杀尊亲属罪应即撤销,并发还安徽高等审判厅更为审判。这意味着,如同前引两则案例一样,大理院再一次以纠错的方式,引导着杀尊亲属罪的司法价值转向:在坚持依法断案的前提下,务求审慎,最大程度地做到定罪、量刑的去特殊化。甚至在律有疑义时,尽量减少杀尊亲属条的适用。如果说在前案中的大理院态度尚处于半肯半不肯之间,那么在此案中,大理院用回避前例的姿态拉开了与立法之间的一段距离。司法与立法之间已出现了某种背离与张力,事实上除了大理院判例,从司法人员的学理解释中也可窥得一二。
四、司法人员的学理阐释司法判决本身是否具有说服力,其背后的一项重要因素是需要有学养深厚、对实务有一定造诣的高素质司法人员群体。作为律法条文与案例之间的重要链接者,司法官在断案时的作为,往往直接关系着普通人的生活走向,而政府的公信力也常常有赖于司法官的表现。时人曾言:“当以一国之政治,其与人民日常关系最切者,莫如司法。政府之得人民信仰与否,亦多系乎法治之隆替。征诸举世而皆然,其于我够尤甚。”尽管未能发掘上述案件中具体某一位署名司法官的个人经历,但仍可以群体推之。清末时期,司法官队伍多由清代刑幕友人员组成,经验有余而新知不足,很难在一夕之间具备现代司法的素养。民国以来,司法职业化的意识和需求都很强烈,北洋政府建立后,司法部于年整顿司法,务求通过对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强调,提高司法官的专业素养。黄源盛教授曾对民国大理院历任院长、推事的基本情况进行列表统计,从而对司法人员素质进行考察。据统计,大理院历任院长、推事79人,学历调查清楚者65人,其中留日习法政者43人、留美法者5人、留英法者4人、出身国内新式法律法政学堂者9人、旧式科举出身者4人。可见大理院推事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新式法学教育,是新式法科人才中的佼佼者。为将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与法学理论的关切相呼应,在这些专业司法人员当中,有的人又能够在综合成文规条、习惯和法理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和法律解释,在当时那个新旧法律转型期间,做出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判决例和解释例,在承担事实造法功能的过程中,结合学理解释去引导杀尊亲属罪的司法实践。由司法职业人员所撰、对《暂行新刑律》进行阐释的法学书籍寥寥,现存有冯国鑫著《现行新刑律详解》,程继元、胡必达编《现行新刑律汇解》,郗朝俊著《刑法原理》等。在杀尊亲属罪的探讨上,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国鑫的一则观点:“所犯重于犯人所知或相等者,从其所知;所犯轻于犯人所知者,从其所犯。”
以犯罪要素论,就杀尊亲属加重其刑情节的认定问题上,毕业于法政大学、先后于晚清大理院及民初地方检察厅任职的冯国鑫在其著《现行新刑律详解》一书中认为,尊亲属与普通人作为不同的犯罪客体,所代表的法律价值不可等同论之。故而,在论杀尊亲属罪名之前,首先需要区分行为人在实施杀人行为之时,是否“仅知犯罪之事实,而未知加重之事实”,着意区分是否存在杀尊亲属之故意。若犯意时不知行为对象为尊亲属,则按普通杀人罪审理:
何谓加重犯罪之刑。杀人者处以杀人罪。若被杀伤者为尊亲属时,各国法律均有加重之明文。新刑律第三百十二条云:杀尊亲属者处死刑。夫杀人为犯罪事实。所杀者系尊亲属为加重之事实,若犯罪者不知所杀之人即为自己之尊亲属时,是仅知犯罪之事实,而未知加重之事实。是亦法律上异其价值之一端也。不知为尊亲属而杀之者,不能因尊亲属而加重其罪。只得科其普通杀人之罪。
冯国鑫不仅以近代西方刑法构成要件对杀尊亲属罪进行学理解释,还援引《唐律疏议》申论之:
按《唐律·名例》云: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疏议曰:假有叔侄,别处生长,素不相识。侄打叔伤,官司推问,始知听。依凡人斗法。又如,别处所盗得大祀神御之物。如此之类。并是犯时不知,得依凡论。悉同常盗断。其本应轻者,或有父不识子、主不识奴。殴打之后,然后始知悉。须依打子及奴本法。不可以凡斗而论。是名本应轻者听从,本明乱律与唐律同。至新刑律第十三条所规定,尤为明显。其第三项之一云:所犯重于犯人所知或相等者,从其所知;所犯轻于犯人所知者,从其所犯。以此观之,今律轻旧律明白包括多矣。
由上可见,以意思责任对犯罪客体加以区别,客观上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行为人的权利,客观上削弱了杀尊亲属罪的特殊地位。结合大理院判决与司法人员所撰写的学理解释,司法界传达的法律价值取向与重视伦常的立法理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很少有司法人员在判决文书中对杀尊亲属的伦理意义展开阐述、对杀尊亲属的犯罪行为从道德层面大加鞭笞。北洋时期的杀尊亲属罪审断,更多地在 行至晚近,杀尊亲属罪的政治意涵已被削弱,势必要为民主平等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做出让步,而其所蕴含的孝道观念被民国政权所保留下来,在民初立法规制中留有一席之地,立法者将其作为重要的传统礼俗给予尊重。
司法者与立法者共同肩负杀尊亲属案件走向近代化的任务。一方面,以新颁行的刑律去纠正原审法院的审理错误,另一方面,发挥司法能动主义以自由裁量权去限缩杀尊亲属罪的司法适用。不完全否定“尊重尊长”和“维持家庭之平和”的家庭伦理立场,尊重本土道德观念的同时,努力将伦理意义与法律意义上的尊亲属人格区分开来,以彰显保护当事人法益及尊重个体人格的刑法理念。
以今论古,民初对传统规则进行调整转换的方式或许尚存讨论空间,但其司法经验和教训都是非常珍贵的。古人云:“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与“俗”从功能上说都对民众生活有规范、指引作用;且习俗乃主要由民间社会自动生成,是内化于民间社会的,和官府加之于民间社会的“法”相比,可能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更实在的规范功能。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曾就此提出“如何使民族本文文化遗留与时进化”“如何使中国国情与外国法制兼容并蓄,如何使怀古之论调与求新求变之学说各得其所”的问题,均有待于刑法学上得到内在的解决。
幸而,法律是长成的。我们的行为规范,虽不是立法者可以制造的,但立法者制成的法律,对于社会大众的意识却有莫大的社会启示作用,从而足以加速促成其意识之成熟。如何减少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的不适,尤其是在杀尊亲属这一类蕴含传统孝道文化的案件中,如何既不冒进又不失时机,理性而果断地推进法制变革以维持国家法制的稳定性,如何以固有惯习为资源,有分寸、创造性地修正既有法律规则,需要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共同作为。
附表:北洋时期杀尊亲属案例一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